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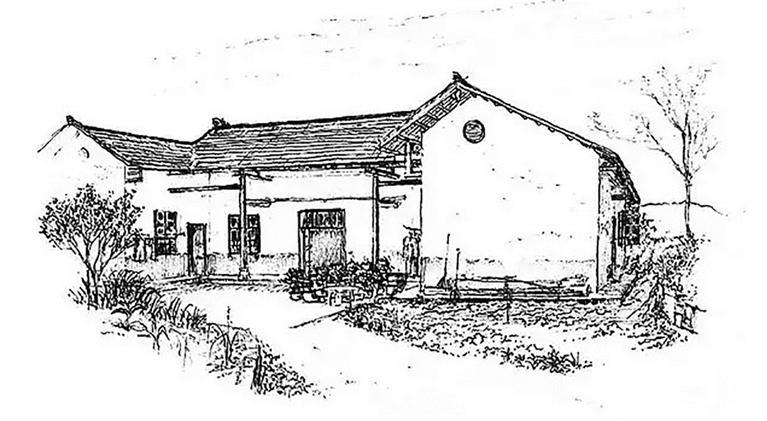
东北的十月已经和冬季的严寒挂钩了。当山海关以南的人还在纠结要不要穿秋裤时,我们已经棉衣加身,火炕一天烧“三顿”了。我小时候,在乡间,夏天为了去除炕上的潮气,要在早上做饭时烧一次炕。进了十月后,天气渐冷,做午饭和晚饭时也要烧火炕,有时赶上雪天,天气骤降,还需将屋里的火炉生着。旧时,物质匮乏,农村人烧不起煤,大家都烧苞米瓤子取暖。
我小时候就盼着秋天的第一场雪,因为下了雪,父亲便领着我们去屯子里的徐二爷家过雪天。徐二爷会在这天将屋里的火炉生着,炕也烧得热热的,老早就站在大门口等我们去呢。
父亲会从家里带一瓶酒,到肉铺割半斤五花肉,到了徐二爷家,让徐二爷放点豆角、土豆、粉条和五花肉一炖,别提多香了。
我们小孩子吃饭快,吃完饭,我们姊妹便围坐在火炉旁,用烧红的炉盖烤地瓜片和花生。父亲和徐二爷一边喝酒一边聊天,徐二爷祖籍山东,也是闯关东来到东北的,我记事起,他就是一个人生活,逢年过节,父亲总请徐二爷到我们家吃饭,唯独秋天的第一场大雪,父亲要去徐二爷家喝酒。
徐二爷比父亲大三十多岁,属于忘年交,但父亲和他却非常谈得来,徐二爷说起自己的想当年,父亲听得津津有味,虽然我都听过好几次了,特别是徐二爷喝了一壶酒后,说的那些车轱辘话,我都背过了,但父亲还像第一次听一样感觉新鲜。徐二爷见父亲喜欢听,讲得更卖力了。父亲和徐二爷一边喝酒一边聊,能聊一个晚上,我的瞌睡劲儿上来了,他俩还没聊完呢。
我和弟弟困得实在受不了了,便在徐二爷家睡觉,大哥和大姐还有妹妹啥时候走的,我都不知道,至于父亲几点走的我更不晓得了。第二天一觉醒来,屋里还热腾腾的,在徐二爷家睡觉可比在我们家睡觉暖和多了。
父亲说,那是徐二爷怕我俩冷,一夜未敢睡着,不停往火炉里加苞米瓤子,烧了整整一箩筐。我和弟弟在徐二爷家睡觉,太费苞米瓤子不说,还影响徐二爷休息,打那以后,我和弟弟再也不敢在徐二爷家睡觉了,但每年秋天飘下第一场雪,徐二爷便会邀父亲去他家喝酒,还特意嘱咐我和弟弟一定也要去,还交待,晚上留宿他家。
打那以后,秋天的头场雪去徐二爷家住,成了我和弟弟的特定“节日”,徐二爷家不仅有暖房,还会给我们准备很多好吃的。
我十岁那年,徐二爷去世了,从此,秋天的第一场雪,再也没有那么暖的房子,这一天,也变得稀松平常。我问父亲,为何徐二爷一走,也把过头雪天的节日带走了呀?父亲说,因为这个节日是为徐二爷而制定的,他一个孤寡老人,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房子里,秋天的第一场雪,是严寒的第一站,人们对突如其来的寒冷还有些不习惯,我们去他家做客,他才有心情把屋子烧得暖暖的,第一个雪天暖和了,以后的风雪天就好过了。
想起白居易的诗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在风雪飘飞的傍晚邀请朋友来家喝酒,共叙衷肠,借此驱赶孤居的冷寂凄凉,父亲懂得徐二爷的心思,便有了深秋头场雪的约定。